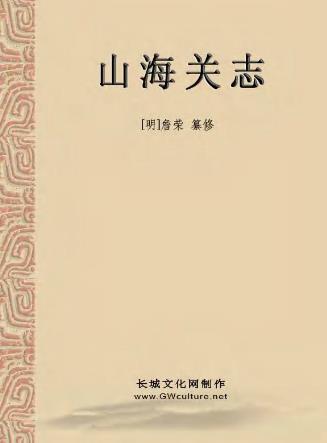县志简介
山海关志八卷 (明)詹榮纂修 明嘉靖十四年(15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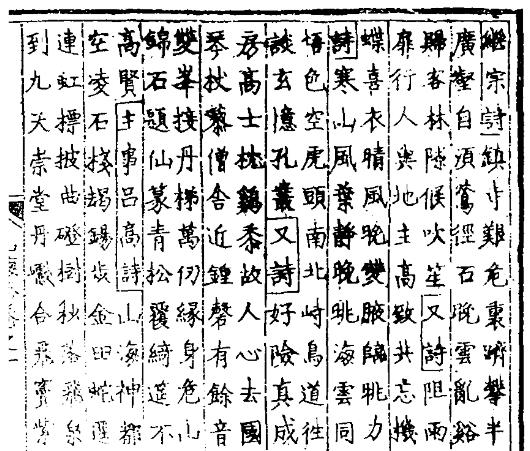
嘉靖山海关志.pdf下载
山海关,“盖畿辅边隘,东括于山海。要之重且大者,亦莫先焉”。《山海关志》是记载山海关地区的专志,从明到清,时人多重视修志。然学界关于《山海关志》的专题研究,目前成果无多。董耀会主编的《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中所收《山海关志》仅对明嘉靖十四年詹荣编纂的《山海关志》做出校注;时晓峰主编的《山海关历代旧志校注》是对山海关旧志收集较全的一部专著,该书收录了五部不同版本的山海关志(包括明嘉靖十四年《山海关志》、清康熙八年《山海关志》、清乾隆二十一年《临榆县志》、清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及民国十八年《临榆县志》),但该书仅仅对五部旧志进行了“文字技术整理”,并未进行实质性研究。窦连起主编的《山海关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当代人编纂的山海关志,其主要内容则是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山海关的变迁,对山海关旧时的记载则相对匮乏。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明清时期《山海关志》各版本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山海关志》各版本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山海关在明清之际军事作用的变迁。
一、山海关志的版本与特点
明清时期的山海关志共有七个版本,其中明朝四种,即: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版、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版、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年版及崇祯十三年(1640年)版;清朝三种,包括清康熙八年(1669年)版、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版、光绪四年(1878年)版。其中明朝的后三版未发现藏本。佘一元(顺治四年进士)所纂《山海关志》的序文详述了明代《山海关志》各版本之流传:
山海旧无志,有之自德平葛公(守礼)始,盖明嘉靖乙未岁(1535)也。葛公属笔于乡先达詹角山先生(荣),公雅重先生,不复更订,随付剞劂。越六十三年,万历丁酉(1597)南城张公(时显)述旧编而增定之,一一出自手裁,视昔加详矣。又历十三年(1610),商州邵公(可立)从而续之,不过补其所未及,匪云修也。至崇祯辛巳(1641),虞城范公(志完)任关道,合所属而重加纂辑,命日《山石志》,其距邵公又三十年矣。
由该序可知,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詹荣所纂《山海关志》,是目前已知《山海关志》的最早版本。由时任兵部主事葛守礼嘱托“同乡先达”——时任户部郎中、山海关人詹荣修撰,并刊刻成书,共八卷。詹荣(1500-1551),字仁甫,山海卫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等职,终官户部左侍郎。嘉靖十三年(1534年)御史张敕巡按山海关时,与时任兵部主事葛守礼共同委托詹荣修志。“荣受命,历五月而成书,凡八条,志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嘉靖十四年(1535年)刊行。该书体例完备,“山海之物,庶几乎登列矣”。该志的修撰弥补了“山海旧无志”的缺憾,具有重要意义。明代的后三种《山海关志》,皆是在此版本上的增订和续修,甚至清朝修撰的志书中仍沿用了该志的部分数据。《山海关志》的第二、三、四版,均已亡佚。由佘序可知,万历丁酉(1597年)张时显再版的山海关志,是在詹荣版的基础上进行增订而成。隆庆三年(1569年)戚继光(1528-1588)练兵蓟镇之时,出于战备方面的考虑,已将山海关由正五品守备镇守的关城升格为由正三品参将把守的路城。加之万历时期因辽事之兴起导致山海关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故此时续修山海关志很大程度出于战略方面的考量。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邵可立(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三版的《山海关志》被清人称为“不过补其所未及,匪云修也”,可知邵版《山海关志》对之前两版的改动不大。而邵氏仅隔十三年便续修《山海关志》,很可能与其当时正在山海关任职并修缮大量关城,因此需要记载此时的盛举以凸显自身政绩有关。崇祯十四年(1641年)范志完(崇祯四年进士)所修之《山石志》与之前各版本相较,应该说是变化较大的版本。因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山海关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同年山海关便由之前的路城升为由总兵把守的镇城,从此山海关成为辽东巨镇,并在整个明清交替之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虽然范氏的《山石志》今已亡佚,但清人在介绍康熙八年(1669年)版山海关志时说:“纂修俱照《山石志》式,其间微有异同。”m。因此对比佘氏所编之《山海关志》,便可窥见范氏《山石志》体例之梗概。且范志完于崇祯壬午年(1642年)就任山海关总督,此时辽东局势已极为严峻,故清人称范氏所修《山石志》“成于抢攘中,多舛错,未经考订””,可见该部志书的修撰质量并非上乘。《山海关志》在清朝共有三个版本,分别为康熙八年(1669年)佘一元纂修的《山海关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钟和梅主修的《临榆县志》及光绪四年(1878年)高锡畴纂修的《临榆县志》。佘一元《山海关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因其修于清朝初年,距离范氏著志仅隔27年。且其问经历过明清易代,佘氏作为明清易代的亲身经历者,同时又是范氏《山石志》的参编人员,因此将其所修志书与明朝所修各志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山海关的战略地位在明清之际的变迁。佘版《山海关志》共十卷,包括对天文、地理、建置、官职、政事、秩祀、选举、人物、艺文、备述十个方面的记载。该书由时任山海关管关通判陈天植、山海路游击陈名远与山海卫守备陈廷谟三人共同委托致仕礼部郎中佘一元编纂清朝新志。余一元,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在接受委托后,余氏“合四志之所载,参以郡乘,采诸群书,访于众见,凡三阅月而书成”。余氏自述编修此志的原因在于自己参与修撰的《山石志》“成于抢攘中,多舛错,未经考订,至今切切于怀”。但更重要的原因实不在此,如陈天植和陈廷谟所言:“中州范公(志完)编有成书,多载胜国旧事。至我世宗章皇帝龙飞辽左,……莫不焕然维新”;“改革以来,山陵川泽犹故也,至于人民之增耗,景物之更移,以及制度之变易,风俗之流转,则有迥然不相侔者矣”,因此有必要“依文章风俗汇成一书以上报天子”。然而,由于清朝建立以后,山海关的军事作用迅速削弱,以致乾隆二年(1737年)时被清朝政府裁撤,在原山海卫辖区的基础上改设由畿辅重地永平府管辖的临榆县。这便是之后山海关志改称《临榆县志》之缘由。詹荣与佘一元的两种山海关志的编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对“天道之变易、人事之隆替”做了详细的记载,通过阅读、对比二志,不仅可以对亡佚的志书内容做出推断,还可以较为明显的看出山海关一地在明清两代地位的变迁。
二、明末清初《山海关志》的内容与特点
明清易代之际有三部《山海关志》亡佚,但考虑到余氏所著《山海关志》是“合四志之所载”的集前志大成之作,因此对比詹荣及佘一元的两部志书,亦能从大体上对亡佚各版本的内容进行推测,补亡志之缺。
1.张时显对《山海关志》的增订张版《山海关志》“述旧编而增定之,视昔加详矣”。“述旧编”显然是接续詹荣之版本,然增订之部分,通过比对各志,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山海关部分城、楼的重修与兴建于此间进行,包括镇东、迎恩、奎光、拱辰四楼的重修,以及临闾楼、牧营楼、威远堂及东罗城的兴建;在志书中,显然不可能忽略对此类重要军事建筑的记载。
第二,嘉靖十四年(153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这六十三年间,山海关地区经历了蝗灾、瘟疫、大雨等种种气象灾害和灾异现象,由于古代社会极容易将灾异现象和朝政的得失进行联系,因此气象灾害,饥荒瘟疫等内容也必将出现在志书之中。
第三,此间的六十余年,山海关地区发生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若干重大事件,包括隆庆三年(1569年)改关城为路城并增设参将,大幅提高了山海关的守备规格;嘉靖四十年(1561年)、万历十五年(1587年)及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廷三次增兵山海关,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力量;万历七年(1579年)戚继光、吴惟忠为抵御北族骑兵的冲击在山海关修筑边墙;万历十七年(1589年)增设山海关管关厅;此类军事上的重要变更,作为边地志书,亦不会轻易忽略。
第四,几乎所有的地方志书中,都会包含一些常规项目的记载,包括:户口的数目及增减情况,官员的任职和变动情况,烈女、举人,名宦的概况等,作为詹荣版《山海关志》的续修,张时显亦不会无视以上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张氏志书中对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户口数的记载颇详,余一元仍沿用了该数目,考虑到佘氏对往昔志书都有所了解,且亲历了崇祯年间《山石志》的修撰,沿用万历二十三年户口数的唯一理由便是明朝后续诸志皆缺乏对山海关地区户口的详细记载。
2.邵可立对《山海关志》的续修
邵氏的《山海关志》被余一元称为“不过补其所未及,匪云修也”。可以推知邵氏对之前两版志书的改动有限,因为在余氏《山海关志》卷三《建置》中,马骡、器械使用的仍是詹荣版本中的数据,可见张氏及邵氏对这两处都未曾修改。在余氏《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兵警》中,自万历十二年(1584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都未记载山海关的兵警情况,但此时正是辽东的多事之秋,尤其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后,辽东更是战事连连,绝不可能无兵警之事出现,因此余氏对兵警的漏记理应与邵氏未曾记载该节有关。邵氏对《山海关志》续修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邵氏在山海关任职期间多次主持山海关城楼的修缮工作,由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如镇东楼、迎恩楼、威远楼、望洋楼、奎光楼的重修理应留有详细记载,即便不炫己之功,亦有青史留名之欲;
其二,在佘氏《山海关志》卷五《政事·户口》中记载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户口数,虽然邵氏志书成于万历三十八年,但不排除此处有邵氏的贡献;
其三,与张氏的续修相同,邵氏增补的内容同样包括十三年间志书中常规内容的增订。
3.范志完《山石志》的纂辑
范氏的《山石志》应当为增加内容较多的一部志书。自万历四十六年清太祖誓师反明之后,山海关的局势渐趋紧张,因此可记之事颇多。虽范氏之志“成于抢攘中,多舛错”,但是其增加的内容仍不可忽视。连佘氏在修志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承认范氏的成果,在众多条目之后标明“以上系旧志”。经过仔细比对亦可发现,佘氏所系之旧志除了《山石志》外,并无参照其他志书之可能。范氏《山石志》之增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山海关新楼、宁海城、南、北翼城及西罗城的修建情况;
二是众多高级官员的任职情况,包括万历四十六年始设之督师、经略、总兵,天启元年(1621年)所设之户部驻山海关官员、海运厅官员及山石关内道,天启二年始设之巡抚、理刑厅官员;
三是山海关由路城升格为镇城的情况;四是如前所述之常规的补充性内容,如举人、贡生、灾异、烈女、名宦等。此外,因佘氏《山海关志》的体例与明朝诸版有较大之差异,而康熙《山海关志》“纂修俱照《山石志》式”,可以推知《山石志》的体例较之前几部《山海关志》有明显变化,主要体现在各主要条目前后顺序的调整。
4.余一元对《山海关志》的修补
清康熙《山海关志》是余一元在综合之前四部“山海关志”的基础上进行重修及增补而来的版本。与之前的各版相比,其特点如下:
一是对修撰体例的修改。佘氏的《山海关志》各卷的编排顺序与传统的官修正史几乎完全相同:天文志排在首位,接下来是地理志,之后是官职、选举、艺文等。增加的“艺文”与“备述”二志,为之前诸版山海关志所缺。
二是余氏对于之前的四部志书,尤其是《山石志》有着明显的沿袭,如卷三《建置》中多次在一节结束时,用括号注明“系旧志”、“以上系旧志”、“出旧志张公时显”等注释。通过对比各志,不难发现除明确标注出于某人外,通常引用的皆是自己曾经与修的《山石志》当中的资料。
四、是在卷四《官职志》中较详细地注明了自嘉靖十四年(1535年)至康熙八年(1669年)间历任山海关官员的任职情况,尤为可贵的是详细记载了众多官职开始设置的时间和裁撤的状况。
是在“人物志”中明显增多了对忠臣、孝子、节烈的描述。这可能也与明清易代之际,大量人员的非正常死亡有关。但佘氏对城池的建置、有关军备物资的数量记载及户口、屯田等内容,几乎完全沿用旧志。余氏对《山海关志》增补的主要内容包括:山海关从远古至清朝的历史沿革及行政归属的记载;对明初在山海关的诸位镇守勋臣的增补;因“兵食为政事之大端也”,故增加“积储”、“兵警”二目;选举增人材一目,补前志之缺;极大的充实了名宦一目的内容。
三、从明及清初两部《山海关志》看山海关战略地位的变迁
对比明及清初的几部山海关志,可见不论从清人的记述,还是从官员的名录抑或是军备、建筑的情况都可以极为强烈地感受到山海关在易代前后最大的差别在于战略地位的弱化。在明朝,该地作为辽东门户,被冠以“天下第一关”之名;而在清朝,该地却不断降格直至归入临榆县中,前后相比何啻天壤。陈名远为余版《山海关志》所做之序开门见山的指出:“山海固用武之区也,我大清定鼎以来,易戎马为承平。”并在后文详述了山海关在明清两朝的变化:“明初建关,设一卫,十千户所,领军万人,以侯伯统之。”¨叫从镇守者的品级之高,不难看出明初统治者对山海关防务的重视。然“阙后无事,兵渐分,守渐单”,以致于正德末年,山海关仅有“守把官军一百一员名”。但明朝后期随着边境局势的恶化,山海关的战略地位日显突出。隆庆三年(1569年)戚继光练兵蓟镇之时,“割一片石为界,弁山海”,山海关遂改关城为路城,并设参将,从此“屹然自成一路”。至明朝后期辽东事起,明朝陆续在山海关设置重要的经理大臣,其中包括山海镇总兵、督师经略、山石关内道、巡抚,从此山海关“特为一镇,马步兵丁二万五千人,定为经制,与辽镇等”¨。山海关以一关城,其地位能够逐渐增加到与明朝传统的“九边”之一辽东镇相等,可见明朝后期统治者对山海关战略地位之重视,亦可从侧面反映出此时辽东局势的紧迫。明清易代之后,山海关虽然被称为盛京和北京的“两京锁钥”,但是其战略地位的迅速下降却显而易见。“先是撤镇,以副帅统其众,未几又撤副帅,以一游击领城守营。此后海防为重,撤游击,只存兵马步三百人。”¨这是清初山海关军事力量削弱的基本轨迹。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降清,仍被任命为清山海关总兵。顺治二年因中原战争的需要,高第被调任至河南,山海关总兵由朱万寿接任并担任至顺治六年(1649年)。因该年山海关裁撤总兵,因此山海镇也被取消,之后以副总兵夏登仕统领山海关之部众,但夏亦于顺治九年(1652年)离任,山海关副总兵也随之裁撤。顺治九年之后以城守游击孙承业领城守营,但孙仅在任四年,便因海防需要撤城守营,只留马步兵三百人守关,由一千总统领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年(1737年),山海关最终被裁撤,并入榆林县。从此山海关一直隶属于榆林县的管辖之下,直至清亡。“路当两京之冲”的山海关何以在明清有着迥然不同的境遇?康熙时北平观察使钱世清即谓:“我圣朝绥靖以来,万邦咸宁,所在为乐土。(山海)关介两都之间,尤升平无事,民生不见兵革,靡有烽烟之警,战斗之虞。”军事地位的迅速下降导致政治地位也随之下降,最终明朝时的镇城便并人县中,在整个清朝不再发挥重要作用。从官职的设置,也可以看出明清之时山海关地位的下降。从文职方面来看,明朝后期在山海关设置的众多总督经略,至清朝时完全裁撤;巡抚及兵备道,同样在清朝被完全裁撤。从武职方面看,参将以上的所有高级军官在清朝时期已经完全撤销,仅以一都司统领之。山海关的军备在清朝亦逐渐废弛。明朝时期镇守山海关的部队有两万五千人,而至清朝时这一数字降低到三百人,数目仅为明朝的百分之一;山海关旧有马骡1036匹头,到明朝后期应当更多,然清朝仅备马62匹,仅为明嘉靖时的十六分之一;从火炮器械方面看,明嘉靖时山海关器械共804,910件,而清初仅有三万件,亦为明嘉靖时的二十七分之一;做为练兵之地的演武场,明万历八年(1580年)戚继光修葺一新,清朝时亦废弛。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山海关在清朝已经完全丧失其战略地位。以上通过对各版本《山海关志》进行仔细的比对,不难对已亡佚的三种《山海关志》的内容做出初步推断。从山海关志的各版本的对比也可以看出,自清朝建立后,山海关的战略地位便迅速下降,虽然“天下第一关”的盛名犹存,但其实已然难副。可见作为军事要地,山海关战略地位的升降决定了其在明清之际的迅速变迁。(从《山海关志》看山海关在明清之际的地位变迁,余劲东,中央民族大学)
· 本嘉靖山海关志.pdf下载是PDF电子版不是实体书,PDF电子版可以在电脑、手机上浏览,请您知晓。您可以联系我们查看更多本志的截图。
· 需要本地其他志书(地名志、人物志、水利志、植物志、交通志、教育志、农业志、文物志、工业志、土地志、方言志、民族志等)或文史资料请在网站上方搜索框输入地名或关键词检索(例:洪洞)。
· 在您联系我们之前请务必阅读理解的内容:《网站服务声明》在您联系我们之时即表明您已悉知声明。
· 服务流程:微信或qq转账红包,支付宝支付相关款项,然后我们通过微信、qq或邮箱发送文件。
· 联系客服微信/QQ:247390556(请注明来意) 邮箱a@xianzhi8.com
·全国地方志文史地情资料浩瀚,如果站内没找到您需要的地方志或站外资料请联系客服帮您查找